沂河·名家专栏丨沂河桃李布春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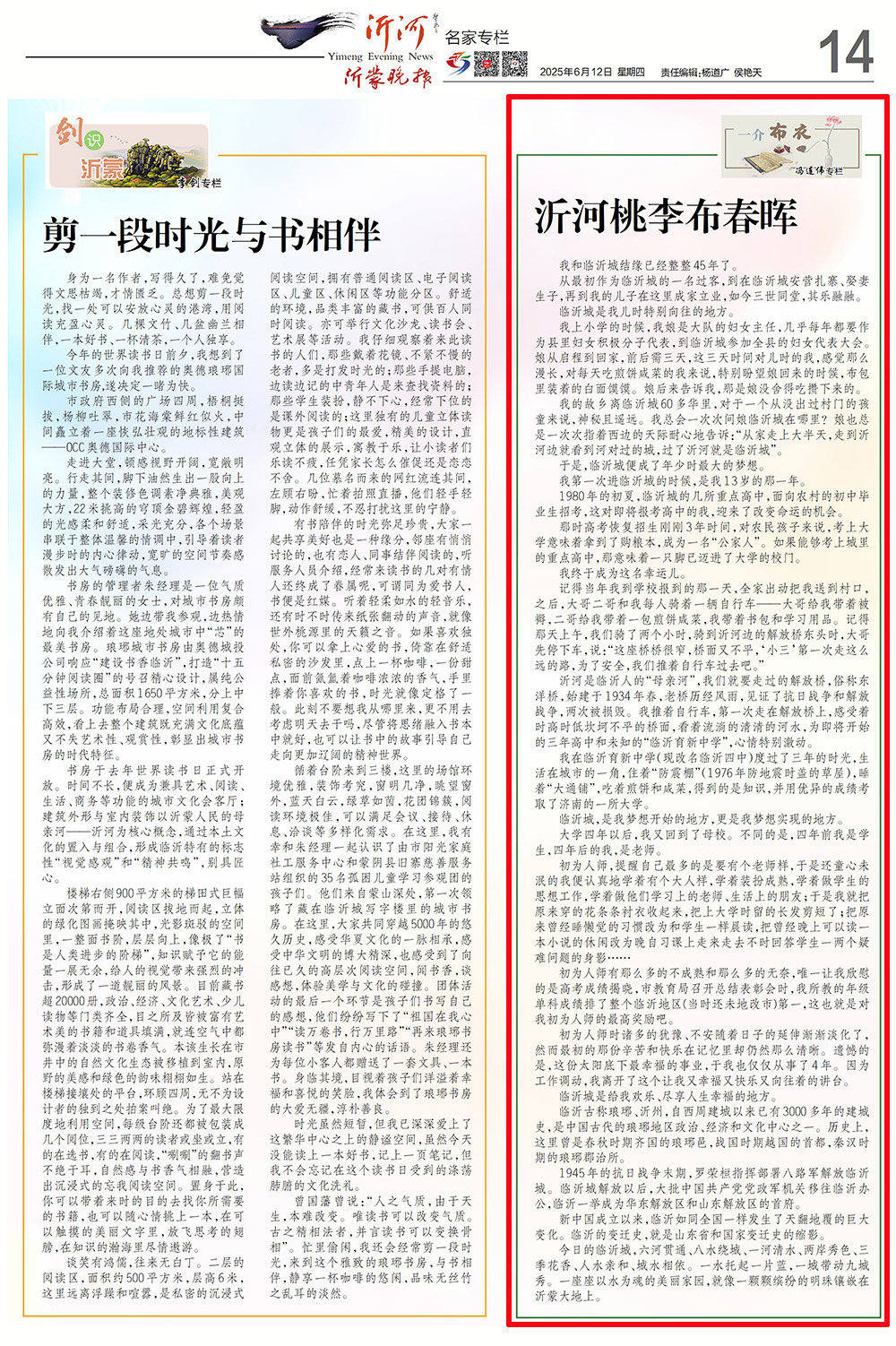
■一介布衣·冯连伟专栏
我和临沂城结缘已经整整45年了。
从最初作为临沂城的一名过客,到在临沂城安营扎寨、娶妻生子,再到我的儿子在这里成家立业,如今三世同堂,其乐融融。
临沂城是我儿时特别向往的地方。
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娘是大队的妇女主任,几乎每年都要作为县里妇女积极分子代表,到临沂城参加全县的妇女代表大会。娘从启程到回家,前后需三天,这三天时间对儿时的我,感觉那么漫长,对每天吃煎饼咸菜的我来说,特别盼望娘回来的时候,布包里装着的白面馍馍。娘后来告诉我,那是娘没舍得吃攒下来的。
我的故乡离临沂城60多华里,对于一个从没出过村门的孩童来说,神秘且遥远。我总会一次次问娘临沂城在哪里?娘也总是一次次指着西边的天际耐心地告诉:“从家走上大半天,走到沂河边就看到河对过的城,过了沂河就是临沂城”。
于是,临沂城便成了年少时最大的梦想。
我第一次进临沂城的时候,是我13岁的那一年。
1980年的初夏,临沂城的几所重点高中,面向农村的初中毕业生招考,这对即将报考高中的我,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那时高考恢复招生刚刚3年时间,对农民孩子来说,考上大学意味着拿到了购粮本,成为一名“公家人”。如果能够考上城里的重点高中,那意味着一只脚已迈进了大学的校门。
我终于成为这名幸运儿。
记得当年我到学校报到的那一天,全家出动把我送到村口,之后,大哥二哥和我每人骑着一辆自行车——大哥给我带着被褥,二哥给我带着一包煎饼咸菜,我带着书包和学习用品。记得那天上午,我们骑了两个小时,骑到沂河边的解放桥东头时,大哥先停下车,说:“这座桥桥很窄,桥面又不平,‘小三’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为了安全,我们推着自行车过去吧。”
沂河是临沂人的“母亲河”,我们就要走过的解放桥,俗称东洋桥,始建于1934年春,老桥历经风雨,见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次被损毁。我推着自行车,第一次走在解放桥上,感受着时高时低坎坷不平的桥面,看着流淌的清清的河水,为即将开始的三年高中和未知的“临沂育新中学”,心情特别激动。
我在临沂育新中学(现改名临沂四中)度过了三年的时光,生活在城市的一角,住着“防震棚”(1976年防地震时盖的草屋),睡着“大通铺”,吃着煎饼和咸菜,得到的是知识,并用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济南的一所大学。
临沂城,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更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
大学四年以后,我又回到了母校。不同的是,四年前我是学生,四年后的我,是老师。
初为人师,提醒自己最多的是要有个老师样,于是还童心未泯的我便认真地学着有个大人样,学着装扮成熟,学着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学着做他们学习上的老师、生活上的朋友;于是我就把原来穿的花条条衬衣收起来,把上大学时留的长发剪短了;把原来曾经睡懒觉的习惯改为和学生一样晨读,把曾经晚上可以读一本小说的休闲改为晚自习课上走来走去不时回答学生一两个疑难问题的身影……
初为人师有那么多的不成熟和那么多的无奈,唯一让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绩揭晓,市教育局召开总结表彰会时,我所教的年级单科成绩排了整个临沂地区(当时还未地改市)第一,这也就是对我初为人师的最高奖励吧。
初为人师时诸多的犹豫、不安随着日子的延伸渐渐淡化了,然而最初的那份辛苦和快乐在记忆里却仍然那么清晰。遗憾的是,这份太阳底下最幸福的事业,于我也仅仅从事了4年。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个让我又幸福又快乐又向往着的讲台。
临沂城是给我欢乐、尽享人生幸福的地方。
临沂古称琅琊、沂州,自西周建城以来已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古代的琅琊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历史上,这里曾是春秋时期齐国的琅琊邑,战国时期越国的首都,秦汉时期的琅琊郡治所。
1945年的抗日战争末期,罗荣桓指挥部署八路军解放临沂城。临沂城解放以后,大批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机关移往临沂办公,临沂一举成为华东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首府。
新中国成立以来,临沂如同全国一样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临沂的变迁史,就是山东省和国家变迁史的缩影。
今日的临沂城,六河贯通、八水绕城、一河清水、两岸秀色、三季花香、人水亲和、城水相依。一水托起一片蓝,一城带动九城秀。一座座以水为魂的美丽家园,就像一颗颗缤纷的明珠镶嵌在沂蒙大地上。
本端所刊登的临沂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媒体作品版权,均为临沂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及作者或页面内声明的版权人所有。未经临沂日报报业集团相应媒体授权,任何网站或组织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复制、编辑或发布。违反上述声明者,临沂日报报业集团所属媒体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0539-8966111
